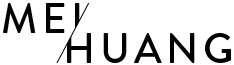古城的当代情怀——特伦多
发表于《艺术商业》2016年12月刊
黄色的土培和巨石器成的堡垒,层层的,紧紧密密的围困着错落古老的房宅。炽烈的阳光照的人睁不开眼,凛冽的冷风却刮的人的皮骨噌噌发疼,脚下的石路湿漉漉的打着滑,每一步都需留意,才不会错踩陡峭的石梯而翻到山下。这是特伦多独有的切肤体验。

她是西班牙的一座百年古城,古卡斯特亚城邦的首都,一度是西班牙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和战略城市之一,其意义不亚于之后建造的政治首都马德里。经历了辉煌、没落再崛起的特伦多,如今是旅游业发展胜地,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名胜古迹游览,特伦多更多的吸引了一群群年轻人、艺术人和文化人的光顾。这是不仅仅是她的饱经风霜的历史的魅力,也由于其独一无二的根据自身文化、艺术和历史出发的古城改建。
古史
站在具有历史的街道上,和站在新城区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历史给了一座城市特殊的魅力。通过呼吸,且听风吟,嘤嘤绕绕在耳边的细言碎语诉说过往的生生死死,悲欢离合,历史变迁。城墙的颜色记录了气候的变幻,火与血的交融。人的整个心态也会变得肃穆起来。特伦多经历了三个拥有截然不同文化的王朝统治,古城区的沧桑与历史感是嬉闹的游人所掩盖不住的。

特伦多的历史应当追溯到西方的铜器时代,也就是大约公园193年。她起先是由罗马人建立的城邦。古代的罗马历史学家依维(Livy, 59BCE-17CE)首次在他的著作中提起了‘特伦多(原著中拉丁语为Toletum)’这个名字,他用拉丁语注释道”urbs parva, sed loco munita”(意为:一个小城市,但地理战略位置优越)。这也是为什么特伦多的基础建筑和排水系统更接近罗马建筑风格的原因。特伦多的基础古建筑浑厚结实,以大理石构成,简单而具有防守功能。城内的角落处也可发现罗马标志性的巨柱的遗骸。由于优秀的战略地位,在穆斯林大举入侵南欧时(公园711年)被穆斯林占据。在穆斯林占领期间,特伦多吸收了很多伊斯兰文化和建筑艺术的精髓。就从城市的地图构建说起吧,穆斯林改良了罗马人的城市卫生系统(在当时,穆斯林文化是地中海文化中最先进的代表文化之一),也扩建和密集了罗马时期相对简单的民居和城市防守系统。这时的特伦多盖满了清真寺,整体的城市也是斜向的,她的整体城池的方向指向麦加——穆斯林的圣地和家乡。1085年,西班牙的狮子和卡斯特亚城邦国王阿尔方多(Alfonso)六世夺回了权位,设立特伦多为卡斯特亚城邦的首都。特伦多成为了天主教城市,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阿尔方多六世领导下的特伦多日渐兴盛,城市的版图也进行了多次的大规模的扩张。首先是天主教堂在被摧毁的清真寺的地基下原地再起,比较有代表性意义的是圣·玛丽大教堂。圣·玛利亚大教堂坐落于特伦多市中心的广场上,是一座具有哥特风格的建筑,巨大的钟楼加上直指天空的穹顶有点像黑暗导演蒂姆·波顿笔下的怪异城堡。另外,阿尔方多六世对特伦多的整个城市结构进行了改良:他调整了穆斯林留下的斜向的城体,使其变为方正的天主教风格;加固了城墙外围,修建了城市顶端的城堡;严格的执行了市民按照等级居住的策略:君主住在山顶的城堡中,阶级等级高的居民住在山上,而平民阶级则住在山脚下,如果你站在山顶俯望古城中的景象,房屋的特质便一目了然。正是这些丰富和不断更替历史的痕迹,造就了今日特伦多城中多文化、建筑与艺术的风貌。
摩登之城
特伦多市政府的官员马尔塔·依斯塔耶在被问到古城规划的问题时说:“在当代,我们的生活习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坏境。也许市政府做的只是尽量合理的去规划用地,而城市中的那些当代的先锋艺术和文化,是自己根据古城的气质衍伸出来的”。
特伦多城市的精神核心犹如隐藏在苍老躯体下的重生的年轻孩童的灵魂,跃跃欲试的将生机与盎然表现出来。曾经读到梁启超因老北京大批古房子的拆除而痛哭流涕,因为在他理想中的规划是在古城的旁边建设一个新城,新城与古城如扁担状,如日月交相呼应,可惜终究是泡了汤。不知是巧合还是梁曾参阅过其他欧洲古城的改建计划,特伦多便是完全符合他理想中要去计划建设的城市。
如今的特伦多,本地中上产阶级早已从古城的中心搬走到古城外新建的新城区中去了。这些市中心的老建筑,自然腾了出来做了新用。政府为了古城改建和吸引游客,大力在这些老建筑里推行艺术和文化。格雷科美术馆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格雷科美术馆的原址是城中一户大户人家的豪宅,在这些人搬走后,市政府收购了这套房子把它改建为特伦多最富代表意义的艺术家格雷科的艺术纪念馆。

格雷科于特伦多,就如高迪于巴塞罗那,毕加索于马拉加,是一个城市的艺术符号。格雷科1541年生于威尼斯,在求学期间深受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影响。他1577年定居在特伦多并创作了很多留世佳作。格雷科的艺术里弥漫着一种宗教崇拜与抵触的矛盾,压抑,严肃和禁欲的色彩。看多了当代艺术无节制的爱与性,格雷科笔下的一张张因饱经痛苦和克制而消瘦扭曲的人脸确实更有看头。他的艺术向我们证明了节制的确比放纵和滥情更高级。不知是巧合还是人为所致,格雷科美术馆的宅邸或多或少的符合了艺术家作品本身的风格:有复杂设计的植物泥土石子路的花园连接着一扇扇幽暗的页窗,层层叠叠的通向曾经为富家主人居室的展厅,展厅的正中挂着面容多疑憔悴的红衣主教的肖像,古老宅子的气息混合着肖像主人那复杂的眼神,仿佛诉说着无尽的故事与沧桑,让观者不禁为眼前的氛围震撼,这是现代“白立方”所不能企及的。
像格雷科美术馆这样由市政府大力资助的美术馆所带来的游客与经济效益,也或多或少的影响了其周边的当代古城街区的艺术文化。在欧洲经济泡沫危机前,市区中心的古建筑租金很贵,因此大多是奢侈品牌的商铺在此聚集。经济危机后,人们的购买力大大下降了,奢侈品和旅游小商品的商铺倒是倒了一多半,留下来的空房子便被之后来此的年轻人们看上了。他们当中的很多是热爱艺术的中青年人,借着市政府大力推广特伦多艺术文化低租金的黄金时段入住这些古宅。
这些年轻人犹如暗处涌动的清流,给古老的特伦多注入了新鲜而奔腾的血液。他们用租下来的老宅创办艺术机构和很酷的艺术餐厅、咖啡厅和酒吧,把古城区的美术馆和历史古迹以点、线、面的形式联系起来。就拿艺术家亥米·米罗开的版画画廊为例吧,他将自己的店铺选址在圣·玛利亚大教堂的北边的一座古宅的一层。画廊的外边并没有挂牌,米罗将房子的外面漆成了蓝色。这个长着红色卷发,一脸剃短的红色胡茬的高大英俊的画廊主有些腼腆的说:“我喜欢这座城市的原因是因为她有她的历史。我喜欢自己早上睁开眼睛,然后喝完黑咖啡走着古老的石子路来上班,感受阳光和特伦多的气息。这些一点一滴小事让我的一天都很愉快。”米罗的画廊很小,只有一间展厅,里面紧凑随性的挂着一些品位相当不错而且价钱公道的版画。他自己也是个艺术家,在不忙的时候也会在大木桌子上自己做些创作,一切都是那么自然真诚。当我问起画廊的经营情况时,他说:“肯定没有像巴塞罗那和马德里那些大城市一个月可以卖出那么多,但是我有我的固定客户,他们有些是特伦多本地的居民,还有一些是德国来此长居的夫妇。把艺术家的画作卖给懂得它们的人是艺术品的最好去处。”
从米罗的画廊向东走,穿过三条横向的长街,我有些转向了。向一位看起来有点中东血统的居民打听回去的路,他问我为何而来,我告诉他我在寻找艺术家们的工作室。“啊,我知道这附近一处地方,很有意思,我带你去。”西班牙人总是这么热情。借着他的引导,我来到了一座贴着古堡的院落。走过土红色和黄色墙面的长廊和郁郁葱葱的古老花园,下了石梯,看到了一处艺术家的工作室。我向我的引路人道了谢,敲了敲门,推门进了工作室。这个工作室有些特殊,里面堆着很多机器。“噢啦(西语的你好),你是?”一位白发的老者询问道,我他解释了我的来意,他很热情也很高兴,他说:“你知道,特伦多以前最著名的产业是什么?是铸剑!我的父亲,祖父,曾祖父和曾曾祖父都是铸剑师。当然了,现在铸剑当然没有什么市场了,于是我读了艺术学院,改行做了雕塑。”他指了指那些机器,“这些使我父亲的机器,是用来给剑和武器印花的,现在我拿它们来做一些小雕塑和首饰。”老者名叫提欧斗娄,他做的首饰和雕塑很精美,但因为是真金白银,所以价格确实不菲。“我还收了一些徒弟们,”他指着窗边一位正在努力打银的小伙子说,“这是吉玛,抱歉他没法和你打招呼,他小时候得了唐氏综合征,但是个有天分的勤奋孩子。”
我的晚饭是在一家名叫“阿玛·德·特伦多”的餐厅里解决的。在路过这家店时,这里的菜单和店内的装修吸引了我。菜单上有四种菜系:天主教、清真和犹太教还有素食者的食物。店子很朴素也很原生态:店子的外观是古建筑,室内装修是用未经打磨的木板和植物拼接而成的。我问门口的服务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菜品的选择,他说:“我们的老板是爱这个城市,他开这家店是为了让人们在原生态和植物中静下心来享受,通过美食记起这个城市的历史与过往。”的确,熙熙攘攘,利来利往,仅仅是这个世界的一面,也有许多人希望过种豆南山,草盛豆稀的慢生活。
结语
特伦多有太多历史与文化可以书写,无奈无法一一介绍道明。细细去品位一个古城的新灵魂也是一桩乐事,我想,其实正如之前市政府的官员所说的,一座古城的当代情怀正是通过她自身的气质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衍伸出来的。古,是沧桑的历史厚重感;年轻的人们则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开拓了自己的新天地。有了从古到今的延续,特伦多这座城市才能持续不断的持续着自身那独一无二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