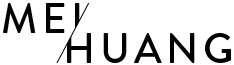撰文:黄梅
本文发表于《艺术商业》2019年7月

然而第一次踏上伊斯坦布尔这片土地的时候是一个人,那个信誓旦旦的男孩我却已经想不起他的全名了。下了飞机,觉得脚下的土地异常陌生。我对这里知之甚少,甚至很难觉得这是亚洲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生在中国西北的人,这里的文化应该与我出生的环境有诸多联系,然而我却很少想起或者思考过西亚,那一次,觉得自己非常的无知。
伊斯坦布尔在东西方交流的历史上一直有重要的地位。例如在丝绸之路上,我们都一直认为意大利罗马是“西方”的终点站,但实际上那是前二、三世纪的事了。在四世纪以后从东方通网罗马和地中海王国的路便由“东罗马”又称拜占庭帝国控制了。在1453年奥斯曼攻占君士坦丁堡后,土耳其人便掌握了控制这条经济命脉的权力,这也为他们累计了巨额的财富。有一种说法是,正是因为避免奥斯曼帝国的高额海关税,西葡二国才开始派人探索新的去亚洲海洋航线,因而发现了新大陆。这也是为什么哥伦布在发现拉丁美洲人的时候把他们叫做“印度人”的原因。
伊斯坦布总体来说是一个明媚的城市,可能与我去的季节有关,印象里,总是炎热的。街上的行人分为两种,一种有着南欧人的长相:白皮肤,浅棕色的稀疏头发,淡色的瞳仁。另一种就更是典型的黄种中东人,与我们的维族和回族人长得十分相似,多毛发茂密,两根眉毛距离很近,弯弯的相连。这样的长相总让我想起大英博物馆里陈列的古美索不达米亚的石雕,男人卷卷的胡子和头发一朵接着一朵卷成像祥云般的一片,杏仁般的眼型和拥有宽阔的肩膀和强壮肌腱的躯体;女人妩媚肉感,拥有花蕾般肥厚的双唇,两条浓密性感的蛾眉弯弯的一直延至蓬松卷曲的发髻。
这里的人是友善好客也是狡诈多端的,就如诸多中东国家一样。交易成功时可以紧紧握住你的手说:嘿,我永远的朋友;转身就给你找一张缺角的纸币。一人出行务必得提起十二分的精神。也因为这样我很少打车,只愿意步行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虽然不便却也给了我更多的机会去感受这个城市。伊斯坦布有两个部分:西部和东部,由一条分割黑海和玛玛拉海的水界分开。西部,正如其名,是更加欧洲化的部分,城区为偏欧式的建筑风格。在这里你可以找的到有机超市,嬉皮咖啡厅,制作各种鸡尾酒的酒吧,水烟厅,艺术机构,和穿着暴露时尚的叼着烟的年轻人。东部则是更加保守的部分,女人还是带着头巾,更有甚者就是高居在阁楼上不下来,要买什么就用竹筐掉个篮子下来请家人或是街坊帮她。餐馆多为清真餐厅。我在东区因为穿短裤背心而被男人跟了两条街,也有保守的妇女跟在背后窃窃私语讨论。这与西区的开放相比真的是天壤之别,如在两个国度一般。
矛盾的激烈碰撞,我认为是这个城市独一无二的魅力。例如蓝色清真寺和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隔街相望。徘徊在这两座史诗级的宗教圣殿之间,我脑中总是出现《天国王朝》中十字军东征夺回圣城的血腥战争和作为基督教领土的最后一站——拜占庭帝国里东正教与伊斯兰王国民族融合的故事场景,那是我十几年前最爱的电影之一。蓝色清真寺庄严坚硬,几何形的轮廓层层叠叠。外面的喷水池里,有穆斯林男人用清冷的泉水清洗赤脚。女人要穿上寺院提供的袍子,遮住四肢和头发的裸露部位,脱了鞋子方能进入。寺内构图庄严,不奉神像,少了有天主教和佛教寺院诸神注视的或柔情或严肃的眼神,你却还是感觉的到空灵之中一双无形之大手的压制。我的伊朗好友曾去麦加朝拜,她回来说自己在朝拜过程中感动的痛哭流涕完全不能自已,需要人搀扶才能行走,我想这大约这就是伊斯兰宗教的力量。地毯老旧却干净,有磨损朝拜的痕迹。空气中弥散着羊脂的辛辣味道。对面的圣索菲亚曾是拜占庭的大教堂。我一直不喜欢中文语言里“教堂”和“大教堂”的翻译,非常不严谨。古拉丁语里教堂是Ecclesia, 大教堂是Cathedrali。 Cathedrali设有中枢主教,统领Ecclesia的所有掌事神父。这两个词有本质的区别,不是仅仅一个“大”字就可诠释。圣索菲亚虽然被伊斯兰教翻修多次,并立上了四根柱塔,却无法掩饰那浓重华丽的血红墙色的拜占庭风格。教堂的旧址上翻建清真寺,清真寺原址拆了再盖更高的教堂,教堂还可以再被覆盖,取决于谁掌握权力,这是欧洲地中海区宗教的一个普遍的特征。圣索非亚的内壁被重新上了漆,但随之时间的推移,这些新漆剥落,露出了东正教的圣像的影子。历史终将示人,没有人和事能够逃得过时间的审判。拜占庭东正的造像相比起天主的文艺复新少了很多柔情浪漫的人文关怀,多了严厉和刻板的审视。这也是中世纪基督教的核心。基督教之所以被当今诸多西方左派人士不齿,大抵是由于中世纪时期引发的大批黑暗战乱。且不谈论基督教分支下的天主教与东正教因争夺权力而致的连年大战,我曾读过一本叫Malleus Maleficarum的中世纪宗教书,翻译过来应叫《女巫之槌》,里面细致的描写了天主教审判长撰写的如何鉴别女巫(或男巫)和残忍的虐杀手段。与其说是杜绝巫术,不如说是排除异己的宗教运动更为贴切。著名刑具如铁处女,即人形外壳的中空铁质塑像,内部布满尖刺将人从头到脚彻底刺穿;或是使人手脚拉伸并从关节处撕断的滚轮床,使我一度对基督教有心里阴影,尤其是“审判者(Inquisitio)”这个词。因为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与其一向以宽容待人和普渡众生温柔示人的形象严重不符。但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得这段历史档案格外有一种扭曲的魅力,正如圣索非亚大教堂那猩红色的墙壁也如温润的血液一般警示着世人所谓“宗教圣人”也会犯致命的错误。
伊斯坦布尔激荡的矛盾不仅仅只存在于历史和宗教,也存在于文化和艺术。先从艺术说起吧。土耳其总体来说是一个保守的国家,然而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确实及其前卫和激烈的,尤其是在当代艺术的实践方面。这与其独特的政治背景有关。在土耳其旅行,你会经常看到一个人的头像,那就是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他是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土耳其人称他为“土耳其之父”。在奥斯曼帝国崩解后,阿塔图尔克带领土耳其国民运动并却在安卡拉建立了独立政府,以其卓著的军事才能解放了国家并且建立了现在的土耳其共和国。在这之后,他进行了一些列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把土耳其从伊斯兰教对政治和教育的影响中脱离出来,确认了与欧盟靠拢的民主的政治方针,伊斯坦布市尔尤其偏向欧盟,以至于当你走在街上有时会感到自己身处欧洲的迷失。由于阿塔图尔克的军队出身,让部分土耳其军队认为把土耳其共和国和伊斯兰教分开是自身的绝对任务。这也使得当身为伊斯兰主义者的现届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想要恢复伊斯兰教的影响时,军方直接的干涉而导致政局一度混乱,成为了土耳其保守势力复苏后当代政变整肃和混沌的开端。
两次双年展:《妈妈,我是野蛮人吗?》或者是《咸水》都是对政治方面的探讨。拿较近的《咸水》来说吧,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在定义此次展览时之所以用“咸水”之名正是因为伊斯坦布尔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和内部冲突,她在访谈里说道:“手机如果掉入淡水中晾干还能是使用,但若是咸水中就不可再用了,咸水具有破坏力,也有改变性。”伊斯坦布尔在黑海和地中海之间,正如欧洲与中东的文明交界之处。 展览正如咸水这种比喻般,带着西方(或是欧洲)前卫和激烈的视角,不断的破坏和冲撞着原有的土耳其传统和伊斯兰文化的影响。给我印象最深的作品场景是在IKSV(伊斯坦布尔文化艺术基金会)的主展场里,一位双性人艺术家裸露着自己生殖器在粉色的烟云中披着羽毛自恋的载歌载舞的影像。像这样的作品我见过不少,但是旁边有一位身着黑色长袍的伊斯兰妇女和他的丈夫在大声咒骂,并且朝着作品吐口水,这点让我很震撼,我差点分不清这是不是作品的一部分,直到他们二人被保安拖走。这个意外的情境给作品加分不少,也很完整的表现了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本身的矛盾性。
在文化方面,这个城市总会给你一种双重错觉。这有点像《开罗时间》里的美国女人初到同为穆斯林城市的埃及开罗时的错乱感。一方面你可以痴迷于异域文化,欣赏着前奥斯曼帝国的雄伟精美的建筑和丰富历史艺术,吃着精致健康的烤肉食物,在水烟厅里和友人喝着美酒抽苹果味的水烟抽到昏天黑地仿佛迷失了时间感。也会被种种保守主义所束缚:作为身着夏日短打的异国女性,被本地男子投来异样的目光或是出言猥琐。或是遇到咖啡厅,门口明确的标出“女人不许入内”的标志。我记得有一年在双年展开幕后一直在派对酒会待到快要天明,在凌晨3、4点打到一辆出租车回酒店,司机大约没有见过亚洲女性一人如此晚的乘车,顿时如打了鸡血般的来了兴致,手舞足蹈的用他蹩脚的英语与我尬聊起来。驶到酒店附近,他大叫着:Look! Look! She is a he (你看!你看!她是个男的),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一位身着妖艳精致的站街“女”郎,浓妆和假发下面,居然是俊朗的男孩面庞。我问司机这正常吗,他说,这很正常,在这女人卖淫会受到惩罚,男人则不会。而且男孩更受欢迎。这让我瞬间想起了主展场里的那件作品,原来这不是仅仅是艺术,是凌晨的伊斯坦布尔在夜色的阴影下那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这便是我回忆中伊斯坦布尔了。它不是黑白分明的,相反,有浑浊的记忆混沌感,这大概是我认为这个城市迷人的地方。那一晚,我终于站在了灯火通明的渡口处,并且暗暗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我还会再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