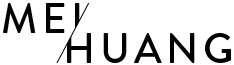——翠西·艾敏与她的艺术
发表于《艺术芭莎》2016年3月封面专辑
的确,对英国当代艺术有所了解的人没人不知道艾敏的床。1999年,刚刚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辍学的她凭借这件作品囊获了当年的特纳大奖和在泰特美术馆展出的机会。正如其题目《我的床》,这件装置作品展示的是一个年轻女人最私密的空间——她的闺床。肮脏的蓝色地毯上,凌乱的散落着用过的避孕套、有咖啡渍的报纸、走形的拖鞋、烟头、打火机、穿过的内裤、咬过的食物和陈旧的小狗毛绒玩具;床上的旧床单与发灰的毛毯还有一条肉色丝袜卷在一起,透出一股浓重的荷尔蒙和生活的气味,与那时美术馆的中产阶级的精致的调子格格不入。这件作品已经展出便引起了英国民众的剧烈讨论,猜想的到,大多是消极极端的评论。“哈,这是艺术吗?我也可以做这样的作品!”,“不论它是不是艺术,我都不会把自己最私人的空间展现给别人的,好恶心!”,还有当时的《周日独立报》十月二十四日的专栏用整版篇幅来质疑这件极其富有争议的作品。当然,也有人给出了积极的声音,有不少艺术评论家发表文章赞美艾敏敢于打破艺术常规的智慧,也有观者感叹这个年轻女艺术家的勇气惊人。不过艾敏自己却并不在意,“我只是表现我自己的生活,传达我想要传达的信息”,她说,“我才不关心别人怎么看,我的自身要比我的作品精彩的多。”
在她1995年创作的《每一个和我睡过的人,1963-1995》中,艾敏把每一个与她睡过觉的人的名字都贴进了一顶蓝色的小帐篷里。帐篷的内里四壁黏着不同人的名字,这些名字不仅仅是与她发生过关系的情人,还有她的母亲,母亲的女朋友,艾敏的哥哥等。这顶小帐篷是童趣的,它使人记起年幼时的躲猫猫游戏。帐篷里的名字以一种花哨稚幼的字体排列着,还有类似于奖状的图形方块,这里好像是艾敏心中的一处秘密游戏基地。帐篷的地板是艾敏喜爱使用的忧郁的蓝色,上面用小女孩的粉红色贴着“总是与自己睡”几个歪歪扭扭的字。这件作品使我们看见了艾敏坚强倔强的外表下的内心的那个温暖的小女孩,她在收藏着自己得到的为数不多的爱。这顶帐篷不但是艾敏真实的生活经历,更是她抒发自我情感的媒介。
你把你的手
抚摸过我的唇,仍然
在我的鼻尖徘徊
我身体的每部分,都在
尖叫,我迷失了
我觉得羞耻
我的身体分裂成了十亿份
每一份都
永远,属于你
这件名叫《爱之诗》的作品讲述了艾敏眼中的男女间无比亲昵又矛盾的体验,它是她生活的挣扎和情欲的迷失的产物:期待爱、惧怕爱、索取爱并把自己赤裸裸的暴露给关系的对方,艾敏以独特的女性的敏感视角和艺术形式进行了能量的宣泄。
《美丽的孩子》也是同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不同于前两件,这幅画是由铅笔在纸面绘制的。画面中,还未成熟的女孩赤裸着瘦削的身体,袒露着平坦的胸部,歪着头对观众尴尬的笑着。在女孩的脚边是被反复擦除涂改的男性生殖器官,它直挺的指向女孩的身体。艾敏说,这幅画为的是表现一种“被迫的入侵”,是“不得不在生命中去被动接受的悲伤”。她用艺术与早年的自己对话,通过一种画面叙述的方式打破了记忆中的羞耻和沉默。
年轻的艾敏只是专注的画着,她并不知道未来再以何种姿态等待着她,她只是力图超越自身而找到活着的意义。但是她不知道,一向对她不公的命运女神这次却向她抛出了魅力十足的橄榄枝,她遇到了改变她今后生活的人:收藏家萨奇。当英国的各大媒体版面还在争相报道足球明星贝克汉姆和辣妹维多利亚的婚事的时候,萨奇以150,000英镑的惊人价格买下了艾敏的《我的床》,比她自己的定价足足高出130,000英镑。之后,萨奇为她专门在自己的美术馆举办了群展和个展,伦敦各大主要画廊的老板也相继来她的工作室邀请她加盟他们的画廊。翠西·艾敏从一个伤痕累累、对自己未来迷茫的边缘年轻艺术家,摇身一变,变成了YBA(Young British Artists,英国年轻艺术家团体),变成了主流,变成了知名艺术家。金钱源源不断的冲入她的银行账户,“哦,宝贝,我完全不是局外人了!”当时艾敏一脸兴奋的对英国一家媒体的记者说。
也是一个伦敦的冬天,那是艾敏在白立方的第一个个展。开幕式前,成群结队的粉丝等在画廊门口,不顾寒冷,只为看上她一眼。艾敏下车,快步走进展厅,“翠西·艾敏,我爱你!我爱你!!”一个粉丝大声尖叫道。
艾敏对这种逆袭的转变接受的很快。“那时我参加所有派对,所有”,艾敏说,“那真是一段疯狂的日子”。成功了的艾敏开始了日复一日的酗酒,抽烟,派对和更加开放的私人生活。“那段时间简直不敢相信,我都不能去英国餐馆。如果我去了餐馆被认出来就要与许多人各种握手,完全没办法好好吃饭了,在法国还能好点。”艾敏回忆道。通过各种高端派对,她也结识了各种圈子的成功人士。她甚至开始给英国《独立报》开始写起文学专栏。“我记得那是2005年,我在歌欧乔夜店,喝的非常多,与我最好的朋友《独立报》的编辑西蒙·柯内尔一起。你知道,歌欧乔夜店的环境就是那种毒品酒精泛滥让人特别兴奋的环境,你喝完一杯,就会有人给你下一杯,然后就是下一杯,然后再下一杯,一杯接着一杯…”她说,“我只记得与西蒙唱了几轮喝了几轮后,他靠过来对我说:‘哎,翠西,你是个特别好的作家你知道不?你为啥不来给我们写写专栏呢?’,然后我就记得我连滚带爬进了计程车里。第二天中午一点中,我从我家厨房的地上醒来,脸被木地板压的全是横条儿,我胃里特恶心,前一晚上的片段又在我脑子中闪回,那感觉就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艾敏用嘴撕着大拇指的死皮,说,“然后我电话就响了,我把电话从地上捡起来然后爬到床上去接听,是西蒙·柯内尔。他就特简单的跟我说感谢我昨晚同意了他的建议然后希望第二天下午五点的时候收到我的稿子,就这样。”艾敏起初只是花几十分钟在手机上打一个300字的专栏发过去,她说“第一次写专栏真的是惨不忍睹,但后来我花了很多时间想这件事,我发觉我开始明白我为什么要写这个专栏了——很简单,就是以一种艺术家思想的方式去写。它不需要向其他的专栏一样。”艾敏这专栏一写就写了四年,她写她自己、写她的父亲、写她的情人、写情人的身体、写性爱、写生活,由于很受欢迎,这些专栏文章在2011年集合出版了一本名叫《我在一个专栏里的生命》的书。
她在这段时间也结识了时尚教母设计师薇薇安·怀斯特伍德,并成为了她的时尚新宠儿。在2001年的新冬夏广告牌上,艾敏身着怀斯特伍德设计的华丽的丝质长跑,穿着黑色的长袜与亮皮高跟凉鞋;她裸露着大腿,棕色的卷发凌乱的盖在脸上,却遮不住她眼神的锋芒。她的背后是一片暗色的森林,充满了野性和神秘。作为一位频繁跨界当代艺术的大牌设计师,怀斯特伍德认为艾敏的艺术和经历正好符合她品牌的形象。“自我”变成了艾敏的时尚标签,她的对自身经历的表达和探索、以及对自己的爱恋和自负都变成了她的个人特征和吸引人的因素,人们爱她,就连英国女王也亲自接见了她。可以说在艾敏最辉煌的时刻,她的自己本身就代表了英国最当代的时尚和艺术。
“吸烟吗?”我问道,“不,早就戒了,很多年以前的4月1号戒的。”眼前的艾敏眼里已经不再带着曾经在杂志封面或是采访中看到的年少轻狂的神色,她很平静,非常的成熟,也略显疲惫;我注意到她眼角和额头的皮肤已经被时光和经历刻下了深深的印记。的确,时间真的很快,离她在萨奇画廊的第一次展览已经有20多年了。如今的艾敏已经不再是那个天天参加派对的狂野女孩,她戒烟了,也很少再喝酒,只是偶尔去参加聚会,更多时间喜欢一个人待着。她读书,看电视记录片,喜欢背着印有自己家小猫图案的背包。“我还是独身,也没有孩子,”她说。经历过无数情人和三位爱人,她也渐渐放弃了对爱情的期待,转而思考和去干她认为更有价值的事。“现在我思考的更多,我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正在变老的中年妇女,只是纯粹的做着自己的工作。”艾敏的真实,在人人都想证明自己是绝顶聪明的伦敦艺术圈里是不多见到的。
不同于运用“床”或者“帐篷”这样的以成品物件作为艺术媒介,艾敏现在更喜欢“手工制作”。在近几年来,她绘制了很多铅笔手稿和霓虹灯作品。最惹眼的是她2014年创作的《相信你自己》。这件霓虹灯作品的灯管还是艾敏20年前最喜欢的蓝色,但不同于诉说伤痛和抒发对爱情的期待,艾敏写下了“相信你自己”这几个字。经历人生极端黑暗再无比辉煌之后,艾敏的生活和艺术都回归了平静,她也不再诉求外部的力量和帮助了,从而转向了寻求内心的清洗与解脱。繁荣终如过眼云烟,艾敏的《相信你自己》其实是自己对自己说的话,也是一种途径去追求内心的平衡。她也学习新的艺术技能如雕塑和拍摄,在她的工作室有一个未雕完的小猫雕塑,她说:“很多艺术家就是专注于一种创作方式,对我来说我喜欢所有方式,而且我也可以做的很好。艺术方式不过是一种途径而已。”艾敏近来喜欢上了例如猫、马和狐狸等的动物,并且制作了大量关于动物的速写、雕塑和纪录片。她还画一些有关于性的墨水或者是铅笔的小稿子,“我已经很久没有做爱了”,她说“基本不记得是什么感觉,这些画更像是一种记忆吧,让我知道还有这么一回事。”2015年4月,艾敏携带着她的性爱手稿在奥地利的里欧魄德美术馆与她最喜爱的艺术家之一埃贡·席勒的作品做了一个展览,她与席勒虽然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却有着类似的痛苦与情感;艾敏对这次展览高兴极了,“这就像是梦境成真了!”她说。
艾敏的成功其实并不是一个偶然。作为一个艺术家,艾敏的自我定位是极其清晰和明确的,她的起点并不主要是对于金钱与名利的渴望与贪婪,而是通过创作艺术而进行自我探索和情感的抒发,以及对自己过去创伤的治愈。她的作品一方面包含不可替代的真实感与存在感,一方面也具有表演性与艺术性;不可诉说的秘密、艰难而且挣扎的生存以及脱离生命的悲剧是艾敏大多数作品的主题思想,通过把她自身的经验和身体代入她的作品,艾敏展现了她与生活、艺术和自我之间的关系。艾敏出生和成长于一个工人阶级的家庭,她创作的艺术作品也与她的生活背景产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她把例如赤裸裸的金钱、廉价的房屋和家具、流行文化、男女的裸体以及生殖器官和直白的性爱等“低俗文化”(这里指相对于西方中产阶级对艺术的审美)带入了“高级艺术”的中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对于西方固化的中产阶级艺术体系的直接批判。不同于古典油画的写实的色彩和曼妙线条,也不同于源起自法国的现代主义大师们浪漫而多情高雅的格调,艾敏的艺术是粗暴和直接的,是感情化的,是“反智慧”的。很多艺术家喜欢流行文化,也善用流行文化的元素去创作作品,但他们的作品始终是浅表的,因为他们只是隔岸观火般的借题发挥,并没有去真实的体验和生活在这种文化当中去。而艾敏是生存在这种环境里的,她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也是真实的她自己。艾敏把高高在上的“学术艺术”玩成了“街头流行”。“我从来没喜欢过艺术史,”艾敏说,“我大学毕业也没搞清楚文艺复兴究竟是啥玩意儿,我只专注于表现我自己。”她已经发展了自己独特的视觉语言,所有绘画或是装置只要源自她手便会自然而然的带着“艾敏出品”标签。而恰恰是这种真实的表现手法打动了特纳奖的评委们,因为他们看到了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和欲望,以及一个曾经生存在社会底层的女人的痛苦与挣扎。
艾敏的年龄与性别、国籍与她所处的时代也决定了她的创作。真正的艺术从来不会脱离社会,社会也是滋养艺术的肥沃的土壤。艾敏成长的时期,正是英国近代政治最动荡时期。在以玛格丽特·撒切尔为首的保守党为了保全英国渡过经济危机保全右派富人利益而大肆削减福利保障、关闭工厂,使英国大批工人失业,沦为流浪者;并且广投经费参与战争,一度使本来经济就极其萧条的国民与警察和军队不断发生冲突暴动。赤贫流浪者的激增与社会的动荡不安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除英国伦敦以及各大主要城市的经济中心外,城市周边县城与不富裕的小镇的安全隐患令人担忧,抢劫、强奸和偷窃这种动荡的背景下似乎都变的司空见惯了。曾经有一个英国记着问艾敏:“你年轻的时候被强奸,有没有报案?那个人最后有没有被抓住?”艾敏平静的说:“报了,但是警察说这种事经常发生。是啊?谁在乎呢?”艾敏的作品在绘制她自身的痛苦的成长经历的同时实际也间接的反应了她身处的国际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另外,艾敏也受到了1970年间欧洲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冲击与影响。欧洲的第二波女权运动主要是专注于女性在社会地位上和经济上获得全面的平等。在1960年以前的欧洲女性避孕和坠胎以及多配偶制度是受到社会舆论谴责以及全面限制的;于是在1970年间,欧洲女权主义者们为经济独立、掌握生育权利和性自由付出了很多的艰辛和努力。这种影响可以从艾敏的很多作品中找到,例如她对自己性生活的表述、自己身体的裸露和情感的表露都强烈的阐释了对女性自身命运的把握以及对自我的深度眷恋和不可忽视的存在感。也正是因为这两个原因,她的作品引起了英国这一代有类似经历和挣扎的人的强烈共鸣。
英国著名影评人安内特·胡恩说:“或许对于那些因为羞耻而沉默的人来说,最难的事情就是找到一种声音:不是自责而认为自己是丑恶的声音,而是发自内心的,认清自己而召唤真实自我的声音。”我想艾敏和她的艺术就是如此吧,艾敏自身和她的艺术一样精彩,她用她的勇气、担当与创造性谱写了英国当代艺术的又一个传奇。